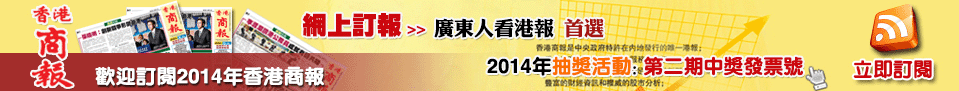回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歷史,讓我們得以窺見貫穿始終的一種強大精神力量的傳承。就福建而言,千百年來海上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多不勝數,人們最為認同和赞賞的是其「包容并蓄,開放多元」的寬闊海洋胸懷。今天,重建「海上絲綢之路」,表達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重建亞太世界秩序、重獲中華話語權的努力。在此背景下回溯往昔,尋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那種不斷開拓進取、創新發展、包容并蓄、多元開放的精神傳承,至今仍深入閩人骨髓,成為引領當代人開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之源。
開啟福建海洋文明 閩商文化走上歷史前台
在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中,以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原文化,長期以來在中華文化中占據統治地位,向來置身化外的東南沿海,多被視為蠻荒之地。然而,隨著時代的更替和版土的擴大,久居中心的中原文化漸漸支撐不了一個龐大的帝國,生存的空間逐漸向海洋拓展,文化的重心亦發生偏移。早在遠古時期已經孕育的中國海洋文明由此浮出水面,與遷徙至此的中原文明交融碰撞,兼收并蓄,構成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元。
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演變中,福建先民勇於開拓進取、向海而生的精神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6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借由簡單的船隻,隨著季風向大洋深處遷徙,他們被后人稱為『南島語族』。這就是閩商的由來。」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文菁如是表示。
閩人向海而生,不斷開拓進取,從最初的獨木舟到慢慢發展起來的具有相當規模的船隊;從最初的出海打魚、自給自足到遠洋貿易發展起來的絲綢之路,一點一滴開拓中國海洋文明的進程,也留給后人無數寶貴精神財富。
蘇文菁向本報表示,古代「海絲」最深遠的影響還在於文化,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同古代「海絲」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由於貿易過程中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斷相遇,使得福建的海洋文化豐富多彩、獨具特色。它包含舟船文化、航海文化、海神文化、宗教文化科從商意識、包容心態及價值觀念等,將其和諧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福建特有的海洋文明。
長期致力於閩商文化與海洋文化研究的蘇文菁發現,宋代的「開洋裕國」,事實上成為整個中國社會價值觀構建的過程,是大國經濟重心轉移的過程,更是培育新社會階層--海商群體的過程。「閩商」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走向歷史的前台。
及至元代,蒙古人的國家政策在兩個方面強化了閩商作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與對國內北方市場的開辟。外籍商人的本地化,首先是將宋代以來閩商的國際貿易網絡進一步擴展與強化;其次,他們的多元化背景加強了閩商的開放性,為閩商在此后的國際化貿易中的作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新「海絲」重構亞太秩序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功地邁入世界強國的行列,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突出,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進一步地提高。作為大國,要想在國際上有很大的話語權,該怎樣做好大國的角色?重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將如何在世界各國中定位自己?
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文菁認為,首先,重走「海上絲綢之路」、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表達的是一個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重建亞太世界秩序、重獲中華話語權的努力。
在蘇文菁看來,海上絲綢之路僅為世界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切入點或者一種說法,但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應拾人牙慧。她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稱為陶瓷之路更為恰當,一個經濟體系對世界產生影響是通過商品作為媒介,而古代中國通過水運輸出陶瓷到東南亞、阿拉伯等各地,對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這個例子可以反映出現今中國話語體系依然圍繞著歐洲話語體系展開,沒有屬於自己的體系中心,因此建立新的話語秩序及以亞洲為中心的新秩序無從談起。重走陶瓷之路,即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是為了繼承當初輝煌時期的經濟體系、文化體系和價值體系,重拾農業文明時代對世界的話語權。」蘇文菁說。
她指出:「重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必須要有兩個姿態:一是重新調整國際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語言秩序,這是重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要努力的方向。第二,中國無論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還是第一大經濟體,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向世界說明,中國經濟能發展到今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歷來就是這樣,這也是中國政府提議重走海上絲綢之路的原因,因為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當時中國在海上或世界秩序的影響力,我們今天是要努力恢復這些輝煌的成就。」
她建議,國家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高到重要的宏觀戰略層面,以海上貿易為切入點,不斷拓展中國的國家戰略,重走海絲之路,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優勢和條件,加強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利用自身經濟發展成果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經驗,重振雄風,實現地區經濟轉型和經濟治理,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她表示,福建是中國最具海洋個性的區域,在建設海洋強國的新一輪資源配置中,特別是「一路一帶」(建設海上絲綢之路與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建設上,應該充分發揚區域的文化優勢與資源稟賦,在提供海洋文化理論、以及歷史遺產資源上起引領推進作用。這是歷史再一次賦予福建的使命與機遇。
多元 包容 開放 進取 孕育閩南人文精髓
閩南的人文精髓深深打上了多元、包容、開放、進取的烙印。而這種精神傳承,與其經濟社會及人口的發展不無淵源。先秦時,閩南本土生活著古越族人,西晉永嘉年間,中原戰火紛飛,「衣冠南渡」的晉民遷徙并扎根於此,帶來先進的中原文明。千百年來,伴隨著各國使節、商人和傳教士的頻繁往來,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東南亞諸多文化在福建廣泛傳播,與中原文化、古閩越文化交匯交融、相生相長,孕育出了獨具特質的閩南文化。
鮮為人知的是,推動刺桐港成為東方第一大港的人物--提舉閩廣市舶的蒲壽庚是阿拉伯后裔。難能可貴的是,南宋偏安政府尚能委令這位阿拉伯人主政泉州市舶司,使這座港口城市的海外貿易到了元代達到鼎盛,贏得世界眾多旅行家禾德里、馬黎諾里、伊本·白圖泰,特別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躬身造訪、馳筆赞叹……
石獅市博物館館長李國宏說,泉州在宋元時期成為世界上第一大港并非偶然。這個古代大港是個開放的大港,一個彼此間尊重,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大港。在泉州人們能看到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宗教,各種各樣的文明相互交融,和諧共處,幾乎沒有冲突。
敢為人先冲破明朝「海禁」
大明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一直堅持古典的朝貢貿易。在中國歷史上,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有輕商的傳統。廣州成為國家許可的惟一對外開放口岸。當歐洲殖民國家紛紛東來的時節,也是當代全球化的開始。明朝卻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面前關起了私人海洋貿易的大門。
然而,東南沿海的閩商開始以各種方式撕開明朝的海禁,延續「海上陶瓷之路」,開始中國的「白銀時代」,使漳州月港成為大航海時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貿易中心。
李國宏就指出,海上絲綢之路不單純只是一條聯繫東西方貿易的航線,而更重要的是一條文化碰撞與文明交融之路。物流必然帶來人流,人流必然帶來文化流,從异域買進來的不僅僅是外國貨物,而是貨物上附載的文化和信息。中國賣出去的陶瓷、絲綢,賣的也不僅僅是貨物,也包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的傳遞。因此整個海上絲綢之路是一種多元的互動。李國宏說:「海上絲綢之路耀眼光環的歷史背后,是沉澱下來的文化。要提煉出文化背后的這種普世
價值,一種彼此之間的尊重和彼此之間的融合,一種美人其美,美美大同的心胸。」他表示,立足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文明的多元、共融出發,彼此之間尊重、吸納,這或許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來說更有普遍意義。
歷史人文現實三大優勢 新福建獨領風騷
201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遴選了9個較有影響力的城市組團「申遺」,在組團的(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北海、漳州、福州、南京)城市中,福建省獨占三席:福州、泉州與漳州。意味著,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遺產方面、在新世紀「重走海上絲綢之路」方面具有獨到的歷史資源與現實意義。
在蘇文菁看來:重走海上絲綢之路、重建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福建具有著歷史的、人文的、現實的三大獨特優勢。
歷史以來,作為中國最具海洋個性的區域,閩人成為從海路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梁與中介。藉助季風、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發的商船持久地、大規模地進入東盟地區;因而使得該區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帶著福建口音的中華文明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廣東區域是明末清代才崛起的對外貿易主要區域。前期,廣東主要是一個吸納海外貿易商的區域;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清政府才允許人民從廣東出洋。浙江沿海的航線主要是北洋區域,且在明清以來的海禁中執行得特別徹底;在對東盟區域的文化影響力較弱。而福建從唐宋以來,一直是中國從海上對外交往的主要區域。唐宋元時代,有福州港、泉州港;宋元年間,泉州港從東方第一大港發展到世界第一大港。明代,在嚴苛的海禁時代,中國官方唯一開放的口岸是福建漳州月港。
由宋元以來福建人大規模的海洋貿易而形成的馬來西亞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馬六甲和檳城與明清時期奉旨「使琉球」的世代福建人居住的琉球王國的五處遺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一樣,表達的是以福建為代表的中國海洋文明在東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今天,該區域不僅是華人華僑最為聚集的地方,且他們的祖居地主要就是福建。這種獨特的文化優勢使得福建與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所經區域之間具有天然的優勢:文化搭台、歷史牽線、經濟唱戲。
福建人不斷地和海外進行的這種交流合作,在迎來送往中漸漸地形成了以文化和血液為紐帶的經濟圈,在發展經貿關系的同時也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對福建本地文化和世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在遷移發展中,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有了更多的交融會合,福建人的足跡遍布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正是這種不畏艱難險阻,勇於開拓進取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