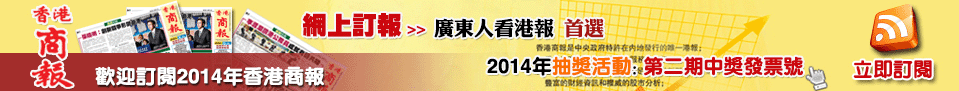當海浪將那個被淹死的孩子冲上恥辱之岸時,世人目睹了兩個大國的歷史角色發生轉換。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稱,美國和德國在重大歷史時刻都經歷過人口大遷徙。但面對移民危機,兩國作出的反應與歷史所預示的可能方向截然不同。
奧巴馬一反常態沉默
面對當今難民的苦難,原本積極的美國總統一反常態地一言不發。與此同時,那些等着接替他入主白宮的共和黨競選人(其中不乏有移民背景者),競相譴責非法移民,紛紛提案「嚴守」美墨邊境。共和黨大熱門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更聲稱要驅逐多達1100萬名非法移民。但另一方面,德國總理卻展現出道德正氣的高大形象,準備安置80萬名難民。僅僅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前,該國的納粹以種族純潔為名,執行了一場最慘無人道的非人化和滅種運動。
美國作為第一個移民國家,自建國以來一貫頌揚其例外主義,但其態度向來變幻無常。對美國生活的著名頌詞之一,克雷夫科爾在1782年發表的《一個美國農民的信》盛赞這個年輕的共和國是全世界唯一無論出身、種族或語言,只要秉持共同的民主理想,移民就能成為公民的地方。但一個世紀后,隨着數十萬名意大利人、東歐人涌入美國,《紐約時報》敲響了最早的「特朗普警鐘」。
美一戰后開啟配額制
1887年5月,就在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禮7個月后,13艘輪船在一日之內載來了1萬名移民,《紐約時報》的社評憤怒地問道:「難道我們就該接納歐洲的貧民?」然而,數以百萬計的難民還是繼續涌來,為美國鋪下種族多樣性的肥沃土壤,20世紀的美國從這片土壤汲取了文化和經濟營養。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氛圍出現了變化。1924年,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史密斯在國會發言時堅稱,「現在我們國內已經有了足夠的人口,可以關上國門,培育純正的美國公民。」
果然美國開始關閉國門,根據當時已經進入美國的非常低的種群比例,執行起無情的配額制度。上世紀30年代,當猶太人面臨滅種危機,拚命地要逃出德意志帝國時,美國對他們關緊國門,使他們被逼入絕境。還是這個時期,加州的墨西哥工人受到暴力襲擊,迫使他們逃回家鄉,還有數萬人被驅逐出境。更糟的是,美國還支持舉行兩場「難民問題」會議,一次是1938年在埃維昂,另一次是1943年在百慕達。當時猶太人遭到大屠殺的恐怖情形已廣為人知,美國在這些大會上捶胸頓足,擠出幾滴鱷魚的眼泪,然而并未拿出任何行動。
歐難民會議忌走過場
因此,德國對敘利亞難民苦難的極大同情异常難得不僅體現於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直截了當(她在對付卷土重來的反猶太主義時也表現出色),還體現於德國民眾的慷慨。或許,正是因為默克爾被妖魔化成令希臘人長期遭受苦難的折磨者才使她認識到,歐盟如果要生存下去,除了充當財政清廉的監督者以外,還需要其他存在理由。又或許,她和德國民眾乃至歐盟28個成員國只是在不經意間迎來這一關鍵時刻。
不管怎樣,這個問題(難民問題,而非主權債務問題)將決定歐洲作為商業周期微調者以外角色的生死存亡。無疑各方將舉行一場會議。但願這次會議不會像埃維昂和百慕達會議那樣走過場。但願這次會議能讓歐洲,包括英國最終發現自己遺失已久的政治骨架:正義脊梁。